尼山會客廳 | 方旭東:分析的儒學是一種新儒學
來源:中國孔子網作者:解放 2024-12-26 17:36
編者按
為持續推動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本色建設,加強新時代儒家思想研究闡發,中國孔子網特推出《尼山會客廳》訪談專欄,邀請專家學者,解讀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時代內涵與當代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日,中國孔子網采訪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方旭東,圍繞分析的儒學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孔子網】您在學術道路上得到了很多大家指導,能否分享一下您與楊國榮教授和陳來教授的師從經歷,以及他們對您學術成長的影響?
方旭東:我的經歷比較特別,在從學過程中先后得到楊國榮、陳來兩位先生指導。在中國哲學界,流傳著“南楊北陳”的說法。了解這兩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學問路數差別甚大。楊國榮先生是馮契先生的學生,馮契先生開創的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傳統,以關注元理論而聞名海內外,而陳來先生則出自馮友蘭—張岱年這一脈絡,后者在民國時代是清華學派的中堅,1952年院系調整后又成為北大中國哲學的主力。陳來先生曾表示,他的工作就是客觀地闡釋中國哲學,而這一學術傳統則繼承自張岱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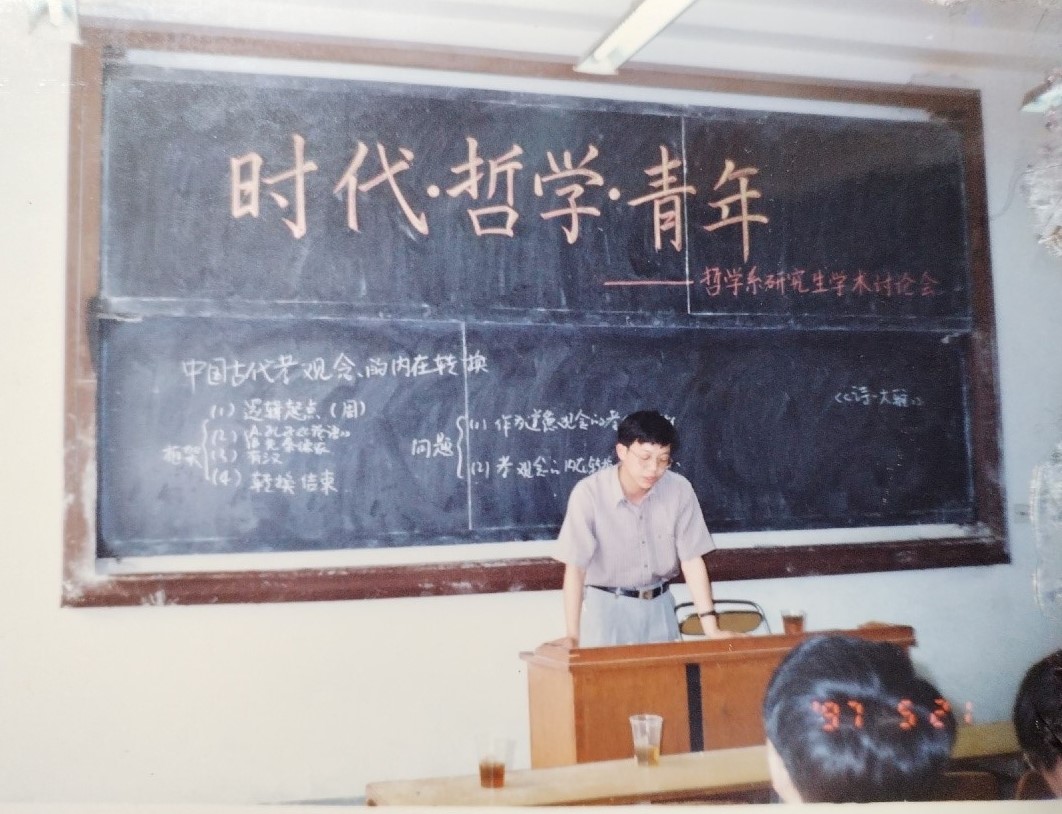
1997年5月21日,在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學術討論會上發言,時為碩士二年級
也許是氣質使然,我對思辨性的形而上學提不起任何興趣,而精確、清晰對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在華師大讀研一時,我讀了兩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其中提到的清人考據工夫深表佩服。同時,我讀了大量英美當代哲學的書,對分析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種興趣最后將我引向對維特根斯坦著作的閱讀。對維特根斯坦的熱情持續了多年,乃至博士畢業后我還翻譯了兩本有關維特根斯坦的小冊子。現在回想起來,碩士階段我能如此沉溺分析哲學的學習,跟華師大中哲尤其是楊國榮先生本人重視西學的氛圍是分不開的,雖然楊國榮先生本人更重視休謨與康德。楊國榮先生對我學術的影響還有更具體的表現,那就是他講陽明的課激發了我對陽明著作的研讀,碩士論文即以王陽明圣人觀為題。在指導學生方面,楊國榮先生的做法是放手,而陳來先生更愿意給學生題目。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吳澄理學思想研究”,就是陳來先生給的。從陳來先生這里,我第一次聽到Scholarship這個詞。這個詞的意思是指一個學者的專擅領域。事實上,陳來先生有意識地把學生朝專家方向培養。那時北大的博士學制還是三年,而在三年里拿出一部研究吳澄理學的博士論文并非易事,吳澄光是文集就有一百卷之夥,另外還有大量經學著作。在北大圖書館古籍部調閱四庫全書當中的《吳文正集》,耗去了我博士階段的大半時光。陳來先生在給我博士論文寫的序中說:本書是對吳澄理學研究最深、最全面的成果,固然是獎掖之詞,恐怕也是他當初對我論文的期望吧。作為先后受教于楊、陳兩位先生的弟子,當初我曾立志要繼承發揚兩位老師的優長,現在幾十年過去了,我不敢說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但捫心自問,我從未放棄這個目標。
【中國孔子網】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儒家思想和道德哲學,特別是“分析的儒學”。您是如何將分析哲學的方法應用于儒學研究的?
方旭東:說到哲學,其實主要有兩種路向,一種是思辨性的,黑格爾哲學是其典型。另一種是分析性的,當代分析哲學不用說了,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中國的荀子、朱子,也都是分析性的。我講的分析的儒學,就屬于這第二種。它不是那么抽象、思辨,而更偏向于日常語言和分析。分析的儒學區別于當代那些思辨性的儒學,一個重要體現,在于它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分析的儒學不憚直面當代的一些熱點問題,尤其是最新、最前沿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分析的儒學是一種新儒學。對于當代出現的這些挑戰,如果儒學不能做出很好的回應,那么,它恐怕難逃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從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儒學的每一次轉型都建立在成功地應對當時社會出現的挑戰之上。
說分析的儒學是一種新儒學,言下之意,它仍然是儒學。其儒學性就反映在:它對很多當代問題、實踐問題的回應是基于一種儒家的立場。比如最近我發表的一篇文章——《伴侶機器人:一種儒家辯護》 ,就是如此。顧名思義,這篇論文不是泛泛地討論伴侶機器人,贊成還是反對,而是站在儒家基本價值的立場上為其做出辯護,主要的接榫點是儒家的夫婦之道。
經常會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我做的分析的儒學“很時髦、很先鋒”,也許在說話者那里“先鋒”并不是什么褒義詞。即便如此,我愿意接受分析的儒學是“先鋒儒學”這樣的帽子。因為我相信,儒學一定是開放的,講儒學的人要跟上時代,要貼近現實,而不是躲進書齋閉門造車,對時事充耳不聞。比如,最近瓊瑤離世,我會關注她留下的遺書,因為其中涉及人是否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倫理話題,而我之前曾經就儒家是否應該支持安樂死的問題跟范瑞平教授有過辯論。
回想起來,我用儒家觀點分析社會熱點問題,起初是“被動”的產物。最早是《東方早報》,后來是“澎湃新聞”,因為有熟人在那里做編輯,時不時會讓我就一些熱點問題發聲。這是一個因緣。另一個因緣是香港城市大學的范瑞平教授,他研究儒家生命倫理學,又編《中外醫學哲學》雜志。自從跟他相識之后,我就經常受他邀請參與有關應用倫理尤其是醫學倫理話題的討論。當然,這些都是外緣。我自身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才是內因,說到底,如果我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純粹出于禮節,頂多也就應承一兩次而已。總之,我對社會熱點有自己的關注,這種關注跟我思考的問題是有內在關聯的,事實上,很多社會新聞都會成為我進行哲學分析的案例。我也可以自豪地說,我是對現實非常敏感的一類學者。
之前《當代儒學》對我做過一個訪談《分析的儒學:不要做開歷史倒車的儒家》 。在那里,我著重談了儒學的進步之維,今天我的講法則強調分析的儒學與思辨的、舊的儒學的區別。儒學總是不斷推陳出新的,就像宋明儒學被稱為新儒學,是因為它經受了佛教的洗禮,回應了佛教的挑戰,相較于先秦和兩漢儒學而為新的儒學。同樣,今天這個新時代也呼喚新的儒學,能夠回應社會變化、科技挑戰的新儒學。分析的儒學之所以出現,也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吧。
前不久《走進孔子》給我做的那個訪談,其中提到,考證也是“分析”一詞的題中應有之義。的確,加上考證這個向度,“分析的儒學”這個概念就變得更厚了。因為“分析的儒學”這樣的名義,在哲學從業者那里似乎更容易聯想到當代西方的分析哲學。其實,考證是中國傳統文史之學的基本功夫。分析的儒學,接引的源頭活水,不止有來自西方的所謂分析哲學,更有中國本土源遠流長的實證考辨之學。這種實證考辨,并非治經的漢學或樸學所專擅,精研性理的朱子何嘗不嫻于此道?《四書章句集注》就是最好的證明。“辨名析理,考鏡源流”,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在研究儒學尤其是歷史上的儒學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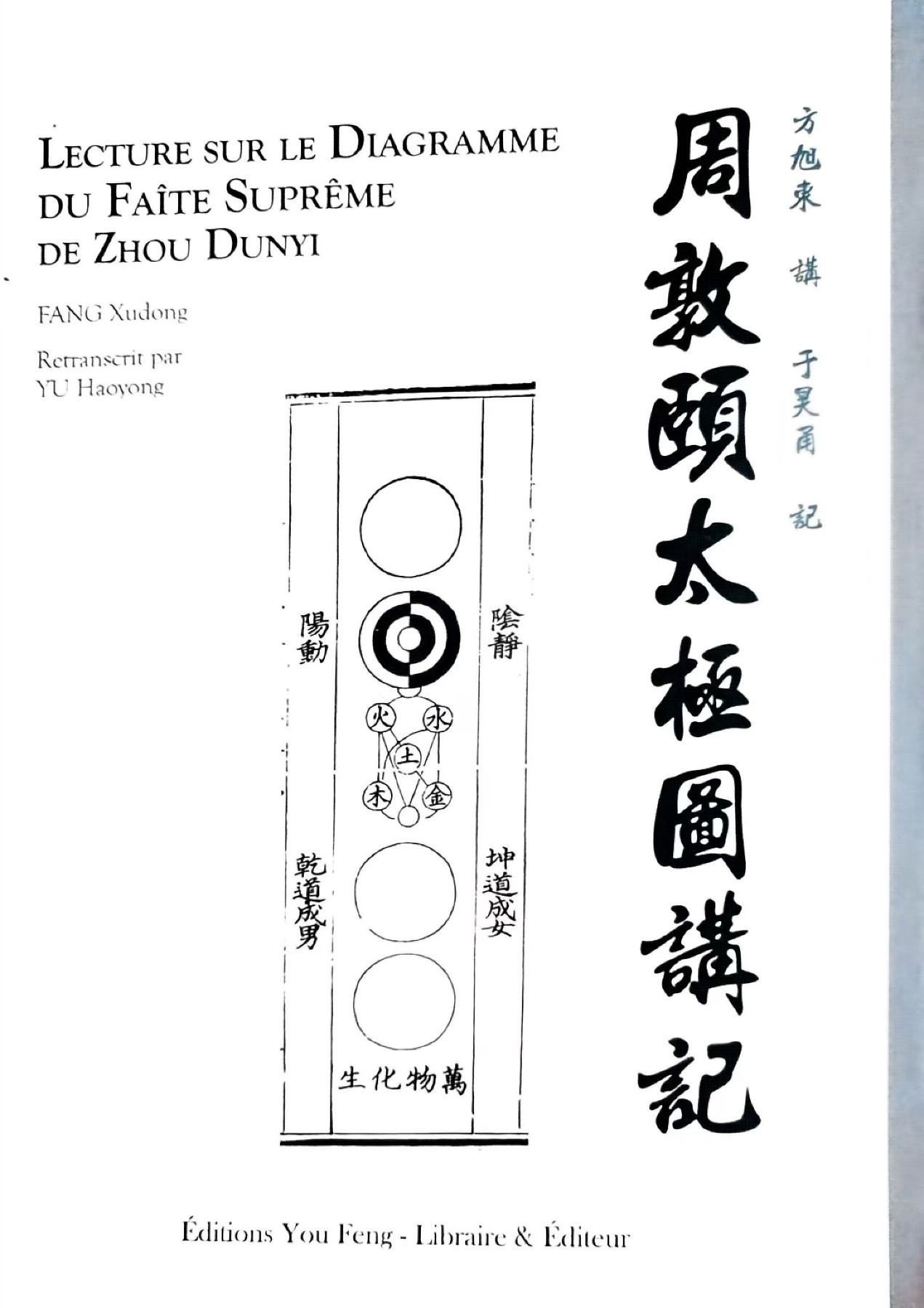
《周敦頤太極圖講記》巴黎版封面
【中國孔子網】您在后果主義的視野下對孟子等儒家經典進行了新的解讀,這種解讀方式對于學習理解儒家思想起到什么作用?您是如何將后果主義與儒家倫理相結合的?
方旭東:從后果主義解讀孟子,是我做的一個個案研究,它屬于哲學史的工作。就學術研究來講,它打破了常人對于孟子的成見。因為一般會認為,孟子講義利之辨,肯定是尚義的,也就是說,孟子的思想可能屬于所謂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或道義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但我通過對《孟子·梁惠王上》首章的分析,對這種陳見提出了挑戰,證成孟子是一個后果主義者。只不過,孟子主張的不是那種頭腦簡單的(simple-minded, naive)后果論,而是一種我稱之為精致的或老練的后果論(sophisticated consequentialism)。
為什么這樣講呢?我們看原文就知道,孟子實際上是告訴梁惠王,如果你一開始就講利,把利作為一個直接目標,就會導致不利于自身的結果。但如果一開始你用仁義去號召百姓,然后百姓講仁講義,有什么好處都會先想到你,即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我對后果論做了這樣一個區分,就可以看出,表面上孟子似乎在批評后果主義,但實際上他反對的只是頭腦簡單的后果論,而主張一種精致的后果論。
這個研究是我對整個儒家進行后果主義解讀的一個部分。這應該是有原創性的貢獻。因為,通常對儒家倫理學的理解是美德論或道義論,而從后果論來理解儒家是比較少的,并且沒有像我這樣對那些關鍵性的哲學文本展開正面的分析。
那么,為什么我要發展出一種對儒家倫理學的后果主義解釋呢?一方面,這個解釋不是我突發奇想,而是建立在之前堅實的個案研究基礎之上。另一方面,這個思路有助于我們解決儒學的一個難題。我們都知道,儒學從本質上講,是勸人行善的。但勸人行善必然會遇到一種詰問:我為什么要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呢?對此,儒家的一個常見解答是,因為你天生性善,也就是說,你本來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孟子式的性善論思路。然而,它的說服力似乎不是那么強。因為,大家在現實中會看到很多人是不善的。對于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儒學,一直以來就存在著一個疑難,那就是要怎么解釋惡的問題。那么,在這個思路之外,我們知道,儒學史上還有荀子的思路。
荀子不承認人性善,但他并不是說要放棄對善的追求。荀子恰恰是站在理性的后果論的角度來證成整個儒家的禮義制度。他設想,人類一開始是處于叢林狀態、戰爭狀態。這個設想跟西方那些講社會契約的哲學家有共通之處。在叢林狀態中,人人都很自私,人人都是利己主義者。人們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發生爭奪,導致總體上結果非常糟糕。這時,人類當中就有一些先知先覺者出現,這些人被稱為圣人。圣人提議,我們要建立一套禮義,把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規范起來,這樣才能有好的結果。其實,在孔子那里就已經講過了。“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了孔子的回答,立刻就明白了,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會秩序亂套,自己也沒飯吃了。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墨家也講后果論,所謂“兼相愛,交相利”。不過,墨家講的后果論跟儒家的有差異。雖然在后果論這一點上,儒墨是可以互通的,是他們相似的地方,但我們也要指出墨家的后果論跟儒家的區別在哪里。區別就在于:墨家不講“差序”。這種差序,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親親、仁民、愛物”。不同于墨家,儒家認識到一個有關人性的事實,那就是:父母可能會為自己的子女做出巨大的犧牲,甚至舍棄自己的生命。的確,這樣的例子很多,很難否認存在這類事實。而墨家好像完全在一種“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講后果論,他們認定,人在跟人“交相利”的時候完全不考慮對方是誰、彼此之間的關系如何。
從后果論角度理解儒家,是基于美德論和道義論不能很好地解釋儒家經典。首先來看道義論。道義論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存在著超乎一切之上的道義或原則。然而,我們知道,孔子以及后來的儒家都會談“經權之辨”。可是按照康德的道義論,沒有“經權之辨”可言。儒家接受權變的根據是什么呢?就是后果。儒家同意,只有整體上有一個更好的后果,才能行“權”,即便破壞了“經”,也在所不惜。再來看美德論。美德論最大的問題是,“美德”是一個有待解釋的概念,換句話說,判斷“美德”的依據要么是道義要么是后果。而且,儒家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贊成美德。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分析《荀子·強國篇》對美德的批評,我把它稱之為“責備美德”。《荀子·強國篇》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叫子發的將軍立了戰功,事后論功行賞,他卻拒絕了封賞。對此,荀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為什么荀子會批評他呢?其實荀子的論證很簡單,就是說子發的做法會引起很不好的結果。比如說,這樣一來,以后大家打仗都不會勇敢了,因為某些人打仗就是為了賞賜去的。無獨有偶,孔子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念。《呂氏春秋》記載,孔子曾經批評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金,贊賞了子路拯溺者而受牛。《論語》記載,孔子評價管仲時認為:“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正是從管仲取得了重大事功的角度肯定其“仁”的,因為據說管仲在私德方面一無可取。如果說“仁”是一種美德,而孔子肯定管仲具有這種美德(如其仁),孔子判斷的依據是管仲的作為產生了巨大的善:比如,避免了流血犧牲,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守護了文明,所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儒家的后果論是審慎的,是經過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它考慮到整個事件的復雜性,并通過周密的計算才得出結果。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待后果論,就可以發現它跟儒家并非水火不容。我們知道,后果論在西方的一個經典形式是utilitarianism,在我們國家它被翻譯為“功利主義”。受宋代王霸義利之辯的影響,“功利”一詞變得惡名昭著。聽到“功利”或“功利主義”,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那種赤裸裸追求個人利益的理論。但實際上,如果我們揭開儒學史,會發現后果主義有多種形式,并不只是粗糙的后果主義,亦有精致的或慎思的后果主義。當然,功利主義也受到很多批評,像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就認為,功利主義破壞了人的人格完整性,認為功利主義對個體要求太多,為了一種從整體上來看最大化的善甚至可以犧牲個體。但是,功利主義或后果論有沒有理論缺陷,跟儒家是否主張后果論,是兩回事。
【中國孔子網】在道德教育中,儒家思想和后果主義各自能發揮什么作用?您認為如何將這兩者有效結合,以培養學生的道德判斷力和實踐能力?
方旭東:如前所述,儒家的道德教育,其實就是勸人為善。鑒于那個元倫理學問題的存在,作為一種道德教育理論,儒學需要回答,人為什么要為善。按照孟子的觀點,人天生性善,所以行善是順其本性。但這種解釋說服力比較弱,因為大家可以明顯感覺到,這個社會有那么多惡人,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說我們天生就是善的呢?而且即便人是性善的,為什么為善還這么難呢?為了達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不得不改變策略,這個策略其實就叫順應現實的人性,即趨利避害,這是人性顛撲不破的定律。如果做好人就意味著受苦受難,一輩子含辛茹苦,像顏回那樣,估計大部分人都不愿做好人了。反之,如果做壞人,一輩子榮華富貴,甚至能夠善終,那大部分人都愿意做壞事了。為此,儒學發展出一種補償理論。比如,孔子那樣的圣人,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德福并不一致,但他的后代世世受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孔子的一種補償。這就對行善得福做了一種承諾。在此基礎上,儒家發展出了一種勸善思想。這個思想非常古老,比如《易傳》里就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是說,做好事會得到好報,做壞事會得到惡報。
這里順便說一下報應論的問題。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有因果報應的說法。但與“報應”相似的觀念在《易經》里就有了,那里叫作“感應”。“感”是你主動發出一個動作(action),然后會收到一個回應(reaction,response),“應”是上天給予的一種回應。所以儒家很早就有“感應”的觀念,只不過,受佛教影響,后來中國民間社會“報應”這個詞用得更多。《太上感應篇》這部在宋代出現的善書,其中的“太上”不是指“太上老君”,據清代惠棟、俞樾等學者考證,太上是指最上、上圣之人,在《曲禮》《春秋左傳》都出現過。《太上感應篇》就是在講,一個人如果做了善事,就會產生好的后果;一個人如果做了惡事,就會導致壞的后果,除了禍及本人還會殃及子孫。這種報應或感應的思想當然是就結果而論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大部分人是不識字的,他們是怎么接受儒家的道德教育的呢?儒家的道德思想在民間究竟是怎么流傳和普及的呢?必須說,善書是一個重要媒介。一些善書還以連環畫的形式出現,就是專門給那些不識字的民眾看的。另外,戲曲當中也有大量的勸善思想。當然,有時里面也摻雜佛教的思想。但就其根本而言,依然沒有偏離儒家“福善禍淫”的理念。
儒家精英們認為,一個人行善不可帶有功利之心。如張載就說“無意為善”,意思是:人不應該帶有任何功利目的去行善。但對普通老百姓來講,這種境界未免太高了,他們是只能接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后世一些儒家進行道德修養或道德教育時,就不得不借助于“功過格”那樣的東西。明代袁黃的功過格非常有名,具體做法是:每天記錄自己的行為,善則記功,惡則記過,到月底會計,年終總結,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功多還是過多,以此督促自己行善累功。袁黃的功過格經常以孝順帶來科舉好運作為善行的證驗。其實,中國民間流行的《二十四孝》,就有孝子以孝感動上天的故事。《二十四孝》當然是儒家思想的載體。
在培養學生的道德判斷力和實踐能力時,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加強后果主義的思維,可能有利于學生提出更富有建設性的意見。比如我在課上曾經舉例,有些人出于同情低收入者的考慮,希望國家對富人征收重稅,用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但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從后果主義考慮,就知道這個想法最后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因為對富人征收重稅,會嚴重挫傷富人擴大再生產、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他們寧可關閉工廠企業,這樣一來,國家不僅征收不到更多的稅,反而還要應對新出現的大規模失業。最后我們會發現,這個政策反而是不利于那些低收入階層的。這個例子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非常直觀的參考。它表明,僅僅抱著所謂善良意愿,很可能會提出一些看起來很美好但實際后果很糟糕很嚴重的提議。
【中國孔子網】您如何看待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的融合問題?儒家倫理中的哪些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方旭東:儒家倫理首先是歷史的產物,在其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所以有一些倫理原則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比如,《論語》中講:“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里仁》)現今,人們已經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能把《論語》這一條當作一種金科玉律,而應該把它理解為一種特殊歷史時期特定社會結構的反映。今天,中國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老齡化與少子化同時到來。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中,如何維護孝道,就不是簡單地照搬傳統可以實現的。試想,如果一對夫妻同時要照顧四個乃至八個老人,怎么可能要求他們像古人那樣盡孝呢?事實上,護理機器人已經被開發出來應用于養老照護。機器人的出現將有效地緩解養老的壓力,但也會帶來新的問題,即便護理機器人能夠很好地替人履行孝道,它跟一個真正的孝子盡孝究竟還有沒有區別?以及:護理機器人的做法是否可以稱之為孝?
這些具體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但無論如何,傳統的儒家倫理必須與時俱進。它們不應當被當作不可改易的教條,而應被視為在當代社會依然有其價值的實踐智慧。關于夫婦的問題,儒家對婦女提出三從四德的道德要求。在今天一夫一妻的社會結構之下,還出現了不婚、不育、不戀的社會現實,該如何去講儒家的夫婦之道,這是需要我們這些研究儒家倫理的人好好去琢磨的,不可能拿儒家的經典直接就用。
雖然儒家倫理學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但我認為這不妨礙它依然能夠對現代社會具有指導意義。比如,儒家對親情、對家庭的強調,這些價值在當代依然值得珍視,雖然當代社會的家庭已經原子化了,甚至出現了新的家庭形態,比如說同性婚姻形成的家庭,還有單身者家庭,這些都對傳統儒家理解的建立在夫婦基礎上的家庭觀念構成挑戰。就我個人而言,一方面對社會變化抱著一種開放的心態,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在現代社會仍有吸引力,有其價值。以儒家所說的“仁”為例。“仁”當然是儒家的一個核心觀念,“愛人”是“仁”的要求,但基督教、墨家同樣強調“愛”,那就要分辨儒家的“仁”究竟有什么特別的主張。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儒家主張的“仁”是“差等之愛”。比如對動物,儒家也認為應該去關愛,但是涉及到價值優先問題時,其傾向于人,則是毫不含糊的。正是這一點使得儒家不同于動物保護主義者,因為動物保護主義者可能會把動物的價值提到人類之上,甚至提到親人之上,那是儒家倫理學所不能認同的。所以,我講儒家倫理學要適應社會新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儒家倫理學可以稀釋到最后沒有一點儒家性的程度。像剛才提到的對親情和家庭的重視就是不能放棄的儒家基本價值。
【中國孔子網】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是否有過跨學科的研究或合作經歷?您如何看待儒學與其他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之間的交叉研究?
方旭東:我嘗試過一些跨學科的研究。比如結合經濟學、政治學、生命倫理學這些學科來研究問題。還有對人工智能話題的探討,其實和自然科學也有關聯。之所以跟這些學科進行交流合作,還是因為儒家倫理必然要回應當代社會的諸多挑戰。我們把當代稱為信息時代,人工智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人文學者,面對現代已經出現的這些事實,我們應該怎么來處理呢?是完全視而不見,只讀自己的圣賢書,還是要適當地給予回應?我認為儒學應該是指導當代社會的一種實踐智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果連當代社會的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都不知道,何談指導?既然有這樣一種意識,就不能不去了解國家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而這些通常是社會科學處理的內容。另外,像探討人工智能、人造子宮、基因工程這些話題,又不得不去了解計算機學科、生物學科的知識,除了不斷去學習,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今天研究儒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第一個挑戰來自社會變遷,另外一個挑戰來自科學發展。前人沒有遇到這樣嚴重的問題,我覺得人文學者、研究儒學的學者,不應該拒斥現代社會的這些信息。如果個人想要回到一種簡樸的生活,當然可以,因為現在垃圾信息的確很多。但是作為研究者的話,如果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有這個能力,當然不能拒絕相關的信息。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