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大典:民俗的典范
來源:中國孔子網作者:常檣 2020-09-23 09:22

時至今日,“孔子文化節”乃“東方圣城”曲阜一年之中最熱鬧最繁華的時段,而其中的高潮部分,則為9月28日(孔子誕辰日)當天在孔廟隆重舉行的“祭孔大典”。2006年,曲阜“祭孔大典”被列入民俗類中國國家級非遺名錄。當下,從民俗學視角來考察和定義祭孔活動,不僅有利于進一步促進對以“孔子”為靈魂為核心的傳統物態文明、精神文明的研究保護和開發利用,更可為推動孔子文化融入時代、深入大眾、走向世界提供難得契機和有力平臺。
民俗堪為民生的美學呈現。民俗,顧名思義,其“民”重在強調民間性、大眾化,意味著其立場和使命在于扎根民生、依托民眾、折射民情、傳達民愿;其“俗”則重在突出作為一種“習俗”“風俗”的穩定性、藝術性,表明其形式和主體必然是多元的、草根的、歷史的、活態的。
由于孔子所開創的儒學長期為歷代政權所推崇,儒學自漢武帝以后便呈現出“德性色彩”與“威權色彩”并重且以后者為主色調的傳揚態勢,因而祭孔也隨之彰顯出極其明顯的官方背景和政治意圖,祭孔長期被小眾化、精英化,且與“民俗”存在很大距離甚至隔閡。正如譚嗣同于19世紀末在《仁學》中所言:“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矣。”但伴隨新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轉型,如民俗專家斷言,當代中國民俗文化的發展模式正從“政府主導型”轉向“社會主導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一轉型也將把 “祭孔大典”推向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鑒于孔夫子在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培育和踐行中華傳統美德中的決定性作用,“祭孔大典”作為一種民俗,便具有了明顯的典范意義。通過走進“祭孔大典”,我們可以管中窺豹,觸類旁通,更好了解我國民俗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現狀、未來走向,更精準把握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傳承模式、社會影響。
偶像的祭禮,有時就是自己的冠禮。
孔子曾告誡他的獨子:“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荀子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論》)在儒家先圣看來,“禮”乃人之為人的大學問,其所涉及的基本項目,與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建構息息相關。祭祀之禮更是強調要通過外在程式化行為來表達對先祖先師或某些被賦予神秘力量和功能的“超人”及類“超人”的感恩崇拜之情。祭禮之形式的神圣、肅穆、整嚴,及內涵的幽遠、厚重、崇高,總能給人以心靈的震撼、精神的洗禮和情感的滌蕩。所以說,參加一場祭禮,特別是像祭孔這樣的隆重祭禮,才是一個人心智得以成熟、擔當精神得以樹立、文化認同得以覺醒的真正開始,這與生理意義上的冠禮給人帶來的觸動和影響,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部“祭孔大典”史,可以從不同角度和側面來解讀。若從民俗學視角來看,其所承載的典范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民族文化認同不斷增強的歷史。
孔子以超凡入圣的智慧和膽量,承前繼后,繼往開來,為中華民族確立起傳統核心價值體系,在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中,他以“素王”“帝王師”之尊,充任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第一位原住民,熔鑄成堅不可摧的中國心,凝聚起一脈相承的中華魂。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去世后,弟子圍繞其墓聚集而居,按時祭祀孔子墓,這一文教區域被稱為“孔里”。“孔里”大約在今日孔林的位置,這便是中國最早的儒家文化主題社區。司馬遷還記載道:“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后從政。”也就是說,在漢初,官員從政前,要先去“孔里”祭拜孔子,這已成為當時政治上的一種“規定動作”。前195年,漢高祖劉邦經過魯國,以最高禮儀“太牢”祭祀孔子,開啟官方及帝王祭孔先河。據史料載,漢高祖以后,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漢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后周太祖、宋真宗、清康熙帝和乾隆帝等帝王都曾到曲阜祭祀孔子。雖然這些帝王的祭孔,并不一定是在官方確定或民間約定俗成的時間進行,但由最高統治者參加的祭孔儀式,絕對堪稱具有標桿意義的祭孔典禮。同時,歷代帝王也不斷加封孔子本人及其嫡裔,孔家逐漸成為天下第一家族。縱觀歷代尊孔帝王可見,其中不乏少數民族政權的帝王或具有少數民族血統的帝王。孔子在維護民族團結和睦、增強民族文化自覺與自信上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見。荀子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荀子·大略》)官方高調祭祀師者鼻祖,不僅標志著國泰民安、文教昌明,也促進了政通人和、人文繁盛,更推動了以廣大民眾為主體的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構與鞏固。因此我們說,“祭孔大典”歷來具備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完全符合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發展的一般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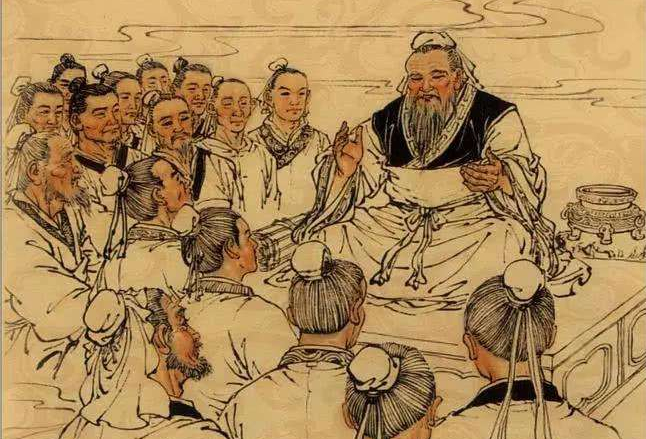
其二,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傳統主流文化在傳承傳播中創新發展的歷史。
孔子在回答子張“十世可知也”這個問題時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大意是說,夏商周三代的禮儀,前后相繼,所增所減孔子都是知道的,以此類推,后世繼承周禮的情況,他也是可知的。此處孔子提到一個重要的文化命題——損益。孔子認為,禮會因時代不同而產生增減(損益),他高度贊同文化在傳承中的創新。但這里還存在著一個潛臺詞,那就是其核心的東西一脈相承,“世襲罔替”。作為傳統中國主流文化的孔子文化,在其發展歷程中,始終秉持原則性與靈活性并重的思路,既要保證其根本屬性和本質特色,又堅持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如孔子在對待先人文化典籍時,“述而不作”,增刪有度,取舍有法,展現出“圣之時者”(孟子稱孔子語)的堅定意志與開放胸襟。自古及今的祭孔典禮,時間不一,形式不同,而作為民俗類非遺的“祭孔大典”,明確于每年孔子誕辰日舉行。與我國古代忌日祭奠先人的傳統不同,于孔誕日舉行最隆重儀式,也不失為對孔子文化傳承傳播中的一大創新之舉。誕辰日舉辦隆重祭禮,弱化甚至消弭了哀思色彩和追悼意味,凸顯出感恩意圖和崇敬姿態,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廣大民眾的參與熱情。
其三,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地方文化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歷史。
民間俗話曰: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民俗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發端于小眾,原本屬于區域性資源,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而孔子文化雖肇始于鄒魯之邦,卻早已由“地方性知識”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今天,“孔子學院”遍及海外,“孔子學堂”遍布國內,雖說其中有借用“孔子”這一象征性符號的意圖,卻也因其“孔子”之名而在普及應用孔子文化上顯得“名正言順”。在新儒家代表杜維明先生倡導的“文化中國”這一大的人文視域下,“孔子”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旗幟性價值和標志性意義。如今,每年一度的孔子誕辰日“全球同祭孔”活動如火如荼。自2016年起,中國孔子基金會依托中國孔子網融媒體平臺,連續多年發起線上“全球同祭孔”,通過信號切換直播包括曲阜“祭孔大典”在內的世界各地祭孔活動,并同時邀請知名儒學專家講解點評,受到廣大孔子文化愛好者、研修者的歡迎與好評。“祭孔大典”作為孔子文化在空間上向外傳播、在時間上向下傳承的一種特色項目和品牌,大大增強了海外華人華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也為新時代愛國主義精神的傳揚搭建起新的平臺和載體。通過對祭孔資料的全面梳理和創新應用,加之互聯網新技術、新媒體的利用,曲阜“祭孔大典”不僅進一步提高了“東方圣城”作為孔子文化濫觴地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更鞏固了齊魯大地在孔子文化傳播應用上的領跑角色,功不可沒!

在未來,作為一種典范意義的民俗,曲阜“祭孔大典”應積極回答好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讓祭孔真正走向民眾,走向民間?一切民俗的最得力傳承人,一定不是個人,而是大眾。“小眾”賦予民俗原初的生命基因,而“大眾”才是其生命偉力的根本承載,如何以民俗形態展現廣大民眾的大美、大善、大愛,真正做到“社會主導”,“祭孔大典”依舊任重道遠。二是如何引領各種祭孔活動并實現各種祭祀活動的“美美與共”?一方面,海內外祭孔活動已呈現噴涌狀,蔚為大觀,相對權威的曲阜“祭孔大典”既要對此進行正確引領,又要求同存異,兼收并蓄,從而保證各地祭孔活動科學理性、嚴肅活潑、與時偕行;另一方面,山東盛產圣人,儒家諸圣外,“科圣”“工圣”“兵圣”“農圣”“算圣”“書圣”“智圣”等都誕生在山東境內,但目前山東對圣人文化資源的研究闡發、挖掘利用可能尚處在初級階段,“祭孔”理當在此方面“走在前列”并提供某些有益借鑒,從而豐富齊魯民俗文化品類,繁榮齊魯民俗文化事業,并進一步為推動新時代中華民俗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做出貢獻。
編輯:解放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