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五講》:與荷花佛法相伴人生
2017-04-17 13:44:00 作者: 來源:中國孔子網(wǎng)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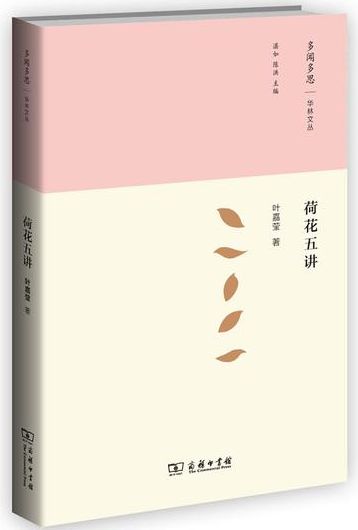
以荷為線,以詩詞為伴,詩詞大家葉嘉瑩先生在新作《荷花五講》中自述與荷花、佛法相伴的人生。葉老在書中坦言自己生于荷月、小名荷花,此生與中國古典詩詞為伴,與佛法有不可思議的緣分。全書文字優(yōu)美,充滿詩情畫意,葉老更在書中圍繞自己經(jīng)歷的家國大事,披露在時代背景下寄情于詩,抒發(fā)內(nèi)心感慨的經(jīng)歷。通過圍繞荷花展開的五次演講,記述了作者一生與中國古典詩詞為伴的經(jīng)歷和與佛法不可思議的殊勝之緣。
第一講《我與蓮花及佛法之因緣》,主要圍繞作者數(shù)次與佛法相遇的經(jīng)歷展開。
第二講《迦陵詩詞稿中的荷花》,則穿插數(shù)首作者本人的得意之作,并多次引用同樣與蓮花有著殊勝因緣的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詩詞,文字優(yōu)美,充滿詩情畫意。
第三講《談我與荷花及南開的因緣》,是作者專門為南開大學(xué)荷花節(jié)而撰寫的一篇文章,其中除了論及荷花,更歷數(shù)了作者與南開大學(xué)之間妙不可言的機(jī)緣。
第四講《我心中的詩詞家國》主要圍繞作者一生經(jīng)歷的家國大事,以及在大時代背景下作者寄情于詩,抒發(fā)內(nèi)心感慨的經(jīng)歷。
第五講《九十歲的回顧——<迦陵詩詞稿>中之心路歷程》是作者對于九十年人生經(jīng)歷的回眸,雋秀話語,飽含了作者與詩詞相伴一路走來的艱辛,也充滿了對過去歲月的無限感慨。

【作者簡介】
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書香世家,南開大學(xué)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dǎo)師,加拿大籍中國古典文學(xué)專家,加拿大皇家學(xué)會院士,曾任臺灣大學(xué)教授,美國哈佛大學(xué)、密歇根大學(xué)、明尼蘇達(dá)大學(xué)及哥倫比亞大學(xué)等校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xué)終身教授,并受聘于國內(nèi)多所大學(xué)客座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名譽研究員。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代表作品有《迦陵文集》十卷、《葉嘉瑩作品集》二十四卷、《王國維及其文學(xué)批評》、《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中國詞學(xué)的現(xiàn)代觀》、《唐宋詞十七講》等。
“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對荷花的喜愛,葉先生在《荷花五講》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不僅僅是因生于荷月而愛荷花,荷花所具有的種種品質(zhì)才是令她傾慕的真正原因。荷花,又被稱為“花中君子”、“翠蓋佳人”,新綻放的荷花還有“出水芙蓉”之美名。《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沒有哪一種植物像荷花一樣周身都有實用價值,其花可賞,根實莖葉都有名字,且每一部分皆有可用,花和葉子可以供人們觀賞;藕可以食用或制作藕粉;蓮子是滋補(bǔ)品;蓮子、藕節(jié)、荷葉都可以入藥。
荷花具有色彩清麗、婀娜多姿的天然美,古人愛荷花,樂府民歌中有“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之句,李商隱《贈荷花》 中贊美荷花“唯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有名的“接天蓮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詩句則出自楊萬里的《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周敦頤在《愛蓮說》中贊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荷花高潔典雅,是君子品性的象征,也指代清麗脫俗的美人、堅貞不屈的愛情。
荷花與佛教更是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佛教視蓮花為圣潔的象征。在佛教中有這樣的傳說:佛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可以開出一朵蓮花,每一朵蓮花之中都有一尊小小的佛像。圍繞荷花所具有的這一些特點和品質(zhì),葉老在《荷花五講》中詳細(xì)講述了一生與荷花、與古典詩詞的因緣。
葉嘉瑩與荷花之因緣
葉老出生于1924年6月,因為6月也被稱為“荷月”,因而小字為“荷”。作為舊時書香世家的小姐,葉先生是關(guān)起門來學(xué)詩詞的,她的父親、母親、伯父、伯母都熱愛詩詞,受到家中環(huán)境的影響,葉先生從小便背誦大量古典詩詞文章,背誦之余更是充滿了對詩詞的熱愛。后她師從詩詞大家顧隨,潛心學(xué)習(xí)詩歌的精魂與生命,在老師的幫助下,葉嘉瑩詩詞創(chuàng)作的造詣逐步提高。
1924年正是戰(zhàn)亂之時,在戰(zhàn)亂中成長起來的葉嘉瑩從小看到的便是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經(jīng)歷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十幾歲的她便開始思考世間的苦難和救贖,15歲時,她作詩《詠荷》:“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她在詩中表達(dá)了對如來的懷疑,蒼生如此不幸,如何才能得到拯救?
1943年秋,為了弄清楚佛法究竟能不能給人帶來救贖,讀大學(xué)三年級的葉嘉瑩到廣濟(jì)寺聽《妙法蓮華經(jīng)》,對佛法一竅不通的葉老記住了“花開蓮現(xiàn),花落蓮成”,意思是:人本來生而具有一顆善良、干凈的可以成佛的種子,可是當(dāng)人在塵世之中生活的時候,人便會‘眼迷乎五顏六色,耳亂乎五音六律’,人要把一切虛幻之中的那個繁華都頓拖、了斷了,真正的種子才會結(jié)成。”受此啟發(fā),葉老后來寫作了一首小詞《鷓鴣天》:
“一瓣心香萬卷經(jīng),茫茫塵夢幾時醒。前因未了非求福,風(fēng)絮飄殘總化萍。時序晚,露華凝。秋蓮搖落果何成。人間是事甚惆悵,檐外風(fēng)搖搭上鈴。”
此后她一心要學(xué)習(xí)佛法,在詩詞中也多用到荷花這一意象。中國歷來有身家不幸詩家幸之說,葉先生所處的動亂時代,造就了她的年少早熟,以及對人世更多的思考與感觸,這些經(jīng)歷與感觸都被她轉(zhuǎn)化為詩歌,汩汩流出。
身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在《荷花五講》中,葉先生詳細(xì)敘述了自己多艱的一生,少時經(jīng)歷戰(zhàn)亂,1948年婚后輾轉(zhuǎn)到臺灣,1949年丈夫因臺灣白色恐怖被抓,后來自己也被迫入獄,出獄后無家可歸只能攜女寄人籬下,生活困頓,她只能靠教書為生。因為詩詞講得好,她被三個大學(xué)聘為講師,那時她每天往返于臺灣大學(xué)、輔仁大學(xué)、淡江大學(xué)教書,上午站三個小時,下午站三個小時,晚上還得站著講課。
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挫折都被她用詩詞的形式記錄下來,作詩以排遣,作詩以忘憂,不需要處心積慮字斟酌句,詩詞自己從她的腦袋里跑出來,這便是大家的厲害之處了吧。到溫哥華后她感慨異國無荷花,此植“不向異根生”,對祖國愈加思念。三十載后終于歸國任教,一顆漂泊的游子之心終于回到了故鄉(xiāng)的懷抱,可喜的是,南開大學(xué)馬蹄湖畔,荷花正好。
葉先生一輩子都在和古典詩詞談戀愛,她對詩詞的講解“闡說精妙,啟發(fā)無窮”,講課聲情并茂,字里行間處處透出她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其著作大多深入淺出,平易近人,有助于推廣詩詞,吸引愛好者,讓現(xiàn)今的人們也能領(lǐng)略古典詩詞魅力,“令人心不死”。在存續(xù)發(fā)揚古典詩詞等方面,葉先生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她站在那里,就是對古典詩歌最好的注解。教書育人七十載,遍歷海峽兩岸,大洋東西,九十高齡仍在培育桃李,傳播中華文化,葉先生的貢獻(xiàn),無人能出其右。